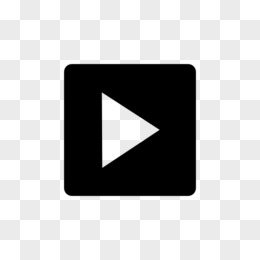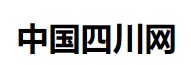在万卷楼景区读陈寿故事。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洪源 摄

宋代白塔,南充重要的文化地标。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洪源 摄

风景优美的阆中留下无数诗篇。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洪源 摄

●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晓江
一座城市的气质,是需要书写的。在嘉陵江畔,有这样一座城市,它是杜甫笔下的“嘉陵江色何所似?石黛碧玉相因依”,是邵伯温描写的“胜地风淳真乐国,四川惟说好充城”,也是陆游书写的“记取清明果州路,半天高柳小青楼”……它就是诗意之城——南充。
南充的精气神在这些古代诗人的笔墨之下散发出迷人的芳香,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浅唱低吟。至现代、当代,与南充有过交集的诗人不胜枚举,有曾经旅居南充的,有在南充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,也有从小在南充长大的。在他们笔下,南充的山水与人文、传统与现代、美食与美景,都在诗歌的香气中弥漫开来。
3月21日“世界诗歌日”到来之际,我们走进南充山水,看古往今来诗人们给这座城市注入了哪些诗意符号?
城——阆中胜事可肠断,阆州城南天下稀
春日,行走在阆中古城的街头巷尾,处处都能感受到古今交汇、诗意充盈的独特城市气质。
与阆中古城一江之隔,有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江山”的锦屏山。杜少陵祠堂便坐落在锦屏山半山腰处,四周古树参天,十分清幽静谧。公元763年至764年,年过五旬的杜甫先后两次来到阆中,停留的时间将近半年,留下诗文66篇,饱含了对阆中的热爱和深情。
杜少陵祠堂的墙上分别刻有杜甫在阆中时的代表作:《阆山歌》《阆水歌》。杜甫在诗中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阆中的偏爱,笔端勾勒如画,书写出阆中绝美的风景。他写阆中的山:“阆州城东灵山白,阆州城北玉台碧”;他写阆中的水:“嘉陵江色何所似?石黛碧玉相因依”。
“阆中胜事可肠断,阆州城南天下稀。”杜甫给阆中古城留下了最美的宣传语,许多人通过他的诗认识阆中、走进阆中。阆中城中的美景尽收杜甫眼底,在杜甫的诗作中有难得一见的闲适与惬意。而阆中的人文风景,给爱国诗人陆游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公元1172年,陆游两次来到阆中。他在阆中盘桓多日,以至魂萦梦绕。他坐船渡江游览锦屏山,瞻仰了杜少陵祠堂,因此写下《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》。诗中前两句“城中飞阁连危亭,处处轩窗临锦屏。涉江亲到锦屏上,却望城郭如丹青。”把三围四面、水绕三方的阆中古城格局,用短短28字描画得活灵活现。
杜甫、陆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都把目光投向了阆中,他们赞美阆中山水,热爱阆中风物。今天,南来北往的人走进阆中古城,在传统与现代之间,仿佛也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营山县作家协会主席李建春,在写出散文诗《阆中古城》之前,专程约上好友到阆中古城住了一晚。
在《阆中古城》中,李建春倾注了对古城的爱恋。他写“阆”字,却说:“城门,一直开着。门内有绣花鞋,有良家女子?”他写落下闳,又说:“长公在上,上善若水。一位老人捧出春节,敬献苍生。”
“阆中去过很多次,但要写好阆中并不容易,它不仅历史悠久,而且文化底蕴深厚,有太多值得书写的内容。”李建春说,阆中文化具有多元性,想通过自己的文字把古城厚重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反映出来,写作过程确实费了一番工夫。
从古至今,阆中的诗歌传奇一直被书写,其热度和色彩依然以其巨大的能量影响着每一个到阆中去的人。
江——千里嘉陵江水色,含烟带月碧于蓝
在公元764年杜甫离开阆中之后,又过了80多年,另一位唐代大诗人也途经阆中。公元851年秋,李商隐在赴梓州(今绵阳市三台县)任职参军时,途经阆中北边的望喜驿,留下了传诵千年的诗作《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》。
泊舟旅途的一天夜里,李商隐住进嘉陵江畔一个名叫望喜的驿站,嘉陵江流向东南方的阆州。当夜,李商隐登楼远眺蜿蜒而去的嘉陵江,想着次日又要启程离开,顿时思绪万千,忍不住吟诗一首,就像挥别老友一样“挥别”嘉陵江:“千里嘉陵江水色,含烟带月碧于蓝。今朝相送东流后,犹自驱车更向南。”
在李商隐之前,公元815年,诗人元稹因得罪宦官,被贬通州(今达州)。当他路经仪陇新政县(今仪陇县新政镇)时,已夜色深沉,漫天繁星倒映在嘉陵江面,像落在了江底,于是有了“新政县前逢月夜,嘉陵江底看星辰。”
元稹一生有两次入蜀经历,第一次时间较短,写有30多首诗,第二次入蜀在通州任职有4年,作诗百首以上,这些诗多有迁谪之感。《新政县》是元稹在仪陇的嘉陵江畔思念友人而作,这位友人不是别人,而是他的知己白居易。
嘉陵江千年流淌,是诗人们抒发情感的载体。嘉陵江也是南充的母亲河,赋予了南充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突出的文化魅力,一代代诗人都把嘉陵江作为吟诵的对象。由诗人曹雷创作、获得冰心散文奖的诗歌《嘉陵江月令》是近年来写嘉陵江的代表作之一。
“日月轮回时,嘉陵江呵,你就是贯穿千年的那一声叹息!”“月令”是上古文章的一种体裁,曹雷用独特的眼光和情感来讴歌嘉陵江母亲河,对诗歌创作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,准确描绘出嘉陵江特有的精神和气质、厚重与轻盈,以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让嘉陵江散发着独特的艺术之美。
嘉陵江之秀美,尤以中游为盛。嘉陵第一江山,山水人文入画屏;嘉陵第一桑梓,稻田桑麻生紫烟;嘉陵第一曲流,山环水绕呈奇观。仪陇县作协副主席庞毅最近在《星星》诗刊上发表了散文诗《嘉陵江与一座城飞奔》(组章),他写道:一条江,走着走着,又拐了个弯。在以她命名的城市,化蝶成一尊楚楚动人的雕像。然后,一起飞奔……
嘉陵江,是南充诗人的灵感之源,也是南充诗人永远的骄傲。
山——远山风雨胜秋色,傍岸烟波起暮潮
嘉陵江岸鹤鸣山,群鹤引颈向碧天。山肩巍峨耸白塔,接云连江数流年。鹤鸣山位于南充城区、嘉陵江东岸,其得名与唐代南充民女谢自然飞升的传说有关,加之山上有建于宋代的白塔,而成为南充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。
“鸡声未报钟先到,催动江城万户烟。”顺庆府通判王以丰曾作诗称赞“白塔晨钟”的绮丽景象,此景色被誉为南充古八景之一。如今,钟声早已远去,但白塔却屹立千年,因着山、水、塔的交相辉映,成为南充的一大名胜。
南充市作协主席、诗人瘦西鸿对白塔情有独钟,他常常登上鹤鸣山,或仰望白塔,述思古之幽情,或俯拾心跳,吟省己以怨怼。也许是塔尖的触角,伸入了诗人的情感世界,于是他写下了《白塔》:“下面肯定有一条蛇/那便是我/我既不兴风作浪/也不敢去爱一个人/最终还是被镇住了。”
无论是游览名山大川,还是忘情山水之间,瘦西鸿唯独对南充的山,有着深入骨髓、涤荡灵魂的爱恋。他迷恋南充的山,不在山的博大高耸,不在山的神秘丰盈,而在于他将其生命与情感、生存与感悟,融入了南充群山。正如他在《在山巅》中写的那样:“在山巅/时间一寸寸矮下去/岁月的经脉/河流一般展开/风声卷起了人群欢呼的泡沫……”
古今之人都爱山,明代南充人陈以勤,号青居山人,就是一种“爱山”的体现。公元1571年,陈以勤辞官回到南充,归家后他徜徉山水之间,每到一处必留诗篇,他以青山的隐士自居,并留下了《青居集》。
青居山在青居场嘉陵江岸,这里有天下奇观359度曲流,历来被人称绝。唐朝姚昂曾经写诗形容“天峙两峰南北峭,地盘一水古今流。”陈以勤一生酷爱青居山,也留下了描写青居山的诗歌,“远山风雨胜秋色,傍岸烟波起暮潮”便是描写青居山的佳句,出自《舟游望青居山》的第二联,对仗工整,视角转换迅疾而分明,上句写青居山在烟雨中迷蒙的景色,下句写暮色中江面烟雾缭绕的美景,远眺近观,触目成趣。
“历朝历代,南充的山山水水,都是文人墨客心中向往的灵魂居所,或畅游、或停留,写下了诸多感怀动容的诗篇。”瘦西鸿说,还有众多的南充本土诗人,流连于山水之间,任性于文字之内,书写了对这方山水的眷恋。
人——从昔遨游盛两川,充城人物自骈阗
从《诗经》到楚辞汉赋,从歌行古风至律词绝句,从诗到词到曲,诗歌每一次形态的变化,嘉陵江都澄澈呈现。一代赋圣司马相如、《太初历》创制者落下闳、“蜀中孔子”谯周、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……这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,都承载着南充文化的深度与厚度,在诗人杨胜应看来,他们就是“最美丘陵在南充排排坐”。
在《星星》诗刊发表的散文诗《最美丘陵在南充排排坐》,杨胜应集中推出了司马相如、落下闳、谯周、陈寿4位历史名人。“大家常说嘉陵江把最柔的身段留在了南充,而我认为南充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,恰似一座座高山,他们共同构成了南充最美丘陵。”杨胜应如是说。
“看了一整夜的星空,他并不打算带走一枚星辰。尽管心里养了一片苍穹,却仍然要回到雨滴敲打青石板的人间生火。”在《落下闳:星辰与烟火》这首诗中,杨胜应通过委婉的语言,展现了落下闳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。谯周,蜀地大儒,杨胜应在散文诗《谯周:推开江水夜读》中肯定了他的智慧:“安乐不再思蜀,这是一个人的良策,同安于天下黎民百姓方才是鸿儒的胸襟。”
在南充历史上,兼具智慧与勇气的,首推纪信。挺身而出、烈火捐躯,这是纪信的选择。他为国为民慷慨献身的伟大壮举,不但成就了大汉四百年基业,也由此让汉族之名走上历史的舞台,其英雄业绩永远值得后人纪念。“纪信生降为沛公,草荒孤垒想英风。”北宋诗人、散文家王禹偁在荥阳古战场一边遥想当年,一边回味历史,在他心中,纪信为汉朝立下“第一功”。
从万卷楼景区大门拾级而上,抬眼望,“万卷楼”金字大匾熠熠生辉,气势恢宏。万卷楼是历史的见证者,书写历史的人便是陈寿。是他,以一己之力钩沉史迹,凭借一部《三国志》书写时代风云。在明代,一位同样名为陈寿的廉吏,他通过吟咏一首《题画》,将自己与史学家陈寿的坎坷心路一并道出:“远道西风落叶寒,萧萧孤蹇上长安。关山不似人心险,游子休歌行路难。”
每一个来南充的人或多或少,在内心中总有一种南充情怀,那便是诗意南充。从杜子美到今天的游人,看到的绝不是简单的自然人文风光,恰如宋代果州知州邵伯温所写的那样:“从昔遨游盛两川,充城人物自骈阗。万家灯火春风陌,十里绮罗明月天。”